九游体育-赵维伦:第一次穿上国家队战袍那感觉太棒了
提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忆20年前我的高中生活
文/秦一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名句,也是我高考那年语文试卷中的一道题目,掐指一算已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但至今仍记忆清晰。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纪念日,也恰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尽管在我心里实在不愿回忆那所读过的高中,但是高中三年的点点滴滴时常在脑海里浮现,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总是有这么一种人生情结驱使着,于是在周年之际提笔纪念,回忆我的老师和同学,与大家分享我20多年前置身学业的苦乐年华。
上世纪那个年代高考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的影响力一点不输于奥运夺冠,时至今日,高考的影响力早不可同日而语了,农村孩子考上高中的人数本来就少得可怜,一旦考上高中就够出人头地了,如果在努力考上大学那简直就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耀了,与高考有关的枝枝节节对每位考生和老师、每个家庭乃至所有家庭成员都是刻骨铭心和终生难忘的,因为那时的高考对农村学子来说不仅仅是跳出农门,还包含有改换门庭意味,谁家家里有考生方圆10里的人都能知道,淳朴的民风民情引导着大家都有心无心为考生操心着,一旦中榜那便是飞黄腾达,一个家族可能从此显耀达贵,如果说城里孩子是努力地学习,那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拼了命的学习,知识改变命运在那个年代着实不是一句假话。
我就读的高中座落于富平县东北部的一个农村小镇上,偏僻又荒蛮,校门是顶部红旗造型的铁栅栏门,刷着浅蓝色油漆,每扇门上都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典型的时代烙印,学校的标志性特征就是紧邻学校大门内按四方形方位矗立着4棵数十米高、几搂粗的白杨树,树荫下掩映着一座红砖结构的工字型瓦房,后来知道那有一间是团委书记的办公室。学校全是带有渭北特色的两檐流水的瓦房,学生宿舍就是一些破旧的教室经过稍微修缮而成,窗户玻璃用塑料纸代替,两排砖垒土填的通铺,中间一条通道,一间宿舍能住40多人,塑料纸时间稍长就星星剥剥,房顶和窗户是雨天漏雨雪天飘雪大风天掀被,不幸的是哪个年代风花雪夜很少、风雪雨却特多,年轻人贪睡,有时候雨雪天醒来不是被子湿了就是满头的雪花。周三或周四之前同学们基本都是吃自家的馒头、条件好的吃锅盔,饭点时的标准动作基本都是一手拿馍一手端一洋瓷碗开水,那个年代几乎没人有专门喝水的杯子,偶尔会有个拿罐头瓶子喝水的,部分同学还拿着大老碗吃饭,以至于万一自己不小心把碗摔碎了可能就没吃饭的家伙了。来自更北部山区来的孩子自带干粮一般要吃6天(那时一周6天),这就是我高中生活的大致框架结构,这一撇生活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来自陈炉镇的陈姓同学拿的那个大黑老碗,典型的古镇特征。工作后多少次和他人谈到这一段生活时,竟然有不少人不相信90年代农村还有这么艰苦的生活,不管你信不信、岁月她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过!面对这样的生活,如果换做现在,大多数学生可能还勉强能受得了,但我想如今的家长肯定是受不了自己的孩子过这么艰苦的生活,因为艰苦、所以至我今记忆犹新。
按常理我们村连片区的孩子考上高中对应的是庄里镇立诚中学,阴差阳错,到我那一届却被分配到了这所高中,一起的同学们一听到这消息,包括家长在内的人个个都不痛快,因为这所学校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还是一块陌生和野蛮的土地,那个年代死板,分到哪只能去哪读,转学几乎不可能,就这样,开学那天怀揣母亲给我准备的125元报名费,二舅用自行车载着我和我的铺盖卷去报名了,记得那天天阴着,天气原因和内心对这块土地的抗拒,因为第二天要上课,所以报完名二舅独自返家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好在没有哭出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在外求学的时光,划开了人生的一个新篇章。
可能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学校才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员,所以上学几年期间,部分有劣性的本地学生动不动就勾结当地好吃懒做的懒汉混混频频来学校敲诈一些外来学生的钱财,不惜武力逼迫外来学生买烟买瓜子等零食,特别是星期日晚上至每周的前三天,因为此时段学生刚从家来,身上带有不多于5块钱的生活费,学校管理也不到位以至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简直是可恨之极,可能本人性情、看不惯欺小凌弱加之亲眼目睹了不少这种事情,所以毕业至今20多年了都难以从脑海里抹去这些带有劣根性的求学插曲、一提到母校首先就想到这些事,以至于离家相距不到20里地,但再也没回过母校。前年春节前因有事刚好路过一次母校,便特意停下车来在大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如今的母校已旧貌换新颜、标志性的建筑和大树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小楼房,隔窗向看门的同志做了个自我介绍,听我是老校友很热情,问了认识的老师,他竟然基本都不认识,我也就递上一支烟顺势走进门房,恰巧有个老人在门房里聊天,看着很眼熟但是叫不上名,后来一聊才知道是我读书期间学校的后勤事务老师,满身老意、青春早已不在,递上一支烟,问问其他老师的情况,认识的老师不是调走了就是退休了,如今母校对我来说几乎没有认识的老师了,是呀,老师们都老了,学校都换新颜了,当年的学生此时也已步入不惑之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按这样的规律新老更替、生生不息,但却把人类的优秀成果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高中卅年的生活真的是要多苦就有多苦,除了学习之外,生活就是排行老二的事情,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烧水的大杀猪锅、玉米珍珍稀饭和教师灶剩余的卜刀面。
不知道现在学校灶上做饭的锅是什么样,当年学校的烧水做饭全用的是农村杀年猪那样的大锅,印象最深的是烧水大锅的锅垢结的很厚,靠近锅沿的一圈锅垢已经炸开,长着大嘴瞅着打水的人,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清理过,当时烧水的老头很牛,动不动就抡个水瓢和学生吵闹起来,因为当时是定时赶点放水,大家都没有热水壶存水,一天喝水就在那几个点打碗水喝,渴极了不跟你干仗才怪呢。开水房是一间坐落在距离学生灶不远处角落里的低矮平房,房子内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灯泡上裹了一层厚厚的泛黄的油性污垢,大锅敞开,锅底有一滩污浊的水,大木锅盖扔在一边,可能只有烧水的时候才会把大木锅盖扣上吧,让现在的人一看绝对会发呕,更别说喝这锅里烧的水了,这环境烧水能不烧出来“肉”嘛。记得有一年夏天晚自习后,天很热,下了晚自习实在是渴的受不了,铃声一响拿着碗就往水房跑,结果跑去后一看黑压压一片人哪能喝到水呀,我这人也不爱挤,就等人群散去,等没人了我们几个人走到锅跟前一看,就剩一底底像白米稀饭一样的水,心想着沉淀一会应该能喝,再不打就只能渴到明天再喝水了,于是拿起水瓢每人打了一碗, 结果出状况了,锅最底有黑乎乎的“肉”显现了,这水还能喝吗 … …,这样的事不知道都发生了多少次,也没人追究,不明真相喝过的学生都完好无缺,没发生过一起集体腹泻等教学事故,可见那时我们穷是穷,但我们的抵抗力是杠杠的。现在的学校都很现代化了,锅炉烧水,至少人手一个热水壶可以确保24小时有水喝,实在不行让饮料上,希望我们的后辈珍惜现如今的美好社会,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
那时候的我们天暖后吃饭喝水基本都在室外,操场、乒乓球案子、教室门前的台阶上、水池旁基本都围一圈人在吃饭喝水,吃饭时间校园里随处三五成群吃饭的同学,嘻嘻哈哈,那一刻都忘记了风雨雪的肆虐,浑身的欢快都凝聚在吃饭上。
大锅熬的稀饭好喝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吧,尤其是大锅熬的玉米珍珍,当年学校灶上卖的玉米大珍子敖的稀饭我至今都难以忘记,或许是因为当年科技还不发达,人性还都很纯真善良淳朴,老品种纯天然无公害的原料玉米磨制珍珍,所以熬出来的稀饭感觉很油、味很长很香,每天早晚都希望轮到自己打饭时玉米珍珍还没断货,多么低的要求,当时母亲给我一周不超过5块钱的生活费,前三天吃冷馍喝开水,吃完了干粮才上灶吃饭,所以说玉米珍珍也不是天天都喝的!基本上我一周花3元左右,也就今天学生的一瓶饮料钱,就这可能还算差不多的家庭。那时候吃饭的资费基本是124两票+122.53毛钱组合,别看少但能吃饱,说到吃不由得就想起教工灶的卜刀面,因为卜刀面炒肉是标配,在那样一个缺肉的年代,偶然花小钱吃几口肉是多么的幸福呀!缘由是这样的:当年学校分教工灶和学生灶,学生灶基本管饱、教工灶肯定是不仅仅管饱还要吃好,于是家庭条件稍微好的、有关系的同学就上的是教工灶,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特权是地位!其他学生只能望洋兴叹咽口水。前面说了我这人干啥都不爱挤不爱挣,赶个晚集图个轻松,因此吃上卜刀面的几率很高,学生打饭排队,值周老师(那时学校专门为学生打饭安排值周老师)端着碗边吃饭边监队,防止人插队,学生灶和教工灶斜对面,我们懒人就在教工灶门口不远处远远站着,一是等人少二是等“卜刀面”的机会,一般老师吃饭早一些,因此,当学生还没吃完饭的时候教工灶基本要准备刷锅了,所以我们这几个不爱站排的人动不动就能等到教工灶那边有人冲着学生灶这边喊“教工灶还剩几碗饭”,因为只有几碗饭,所以我们一听见喊就撒腿跑过去,生怕错过改善生活的机会,因为这碗饭很可能有肉还就掏学生灶的钱,尝到了甜头的学生每天就会有意无意的到时间去捕捉这个机会,这就是我记忆犹新的卜刀面,尽管比不上今天的一份凉皮,但是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农村学生来说就是一顿美餐,至今都觉得很香。
记得那年刚一上高中,老天就小间歇的连续了40多天的阴雨天,从家到学校不到20里路,却是一路土路、更没车,只能靠步行,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一次星期天下午返校时下雨,反正我当时没雨鞋更别提运动鞋了,母亲就给我找了一双露脚趾头、脚后跟磨透了的该扔但还没扔的破布鞋让我穿上,把另一双布鞋装洗衣粉袋子里挂我肩膀上,母亲说到学校了把破布鞋顺便一扔、把脚一洗、把好鞋换上刚好没负担,就这样脚蹬破布鞋头顶蛇皮袋子捏的雨衣、肩扛馍布袋上学去了,途中有一段炭渣路,走一走掏一掏窜进鞋里的炭渣粒,不然会磨破脚,这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全程柏油马路、有公交车、有雨伞、有私家车,那个家长还愿意让孩子受这份罪呀!人类总要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我想说的是:不管苦不苦,农村的子弟们行动起来、把书读好,说对得其父母是套话,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年华那才是大实话。
高中期间还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至今也记忆犹新。那时候每周还是5天半,星期六还有半天。记得事发在一个冬天,周五吃过午饭就没任何资费了,何况午饭还只吃了个半饱,钱也没有了、饭票也没有了,临近周末了,同学们基本也都见底了,没几个人有多余的钱粮,咋办?只有饿,就这样打碗水一喝,一直饿到周六中午放学,本来肚子里油水就很少,那个饿呀… …,刚开始平路还能骑一段自行车,后来几乎一直上坡路,越走越饿,感觉一点力气没有,自行车简直都成了负担,就这么晕晕乎乎地硬撑着赶了了几个小时路好不容易熬到家,一进家门身体似乎也瞬间崩溃了,人和车顺势就倒了下去,我一边喊“妈”,一边说赶紧给我准备吃的,村里串门的邻居惊讶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也知道周六我回家所以提前做好了饭,不记得吃了多少饭,只记得那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吃完饭倒头就睡,如今再回想起来,很佩服自己的身体,没油水的肚子竟然还能这么挨饿!
高中三年还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就是教室。刚入学住了一段时间宿舍外,再后来基本都住在教室里,每学期开学都早早去抢教室的铺位,为什么呢?因为住宿舍总有本地的坏学生聚一堆去宿舍抽烟、糟蹋我们的被褥,因此外来住校生都优先选择晚上住教室,安全、省事且没人来捣乱,那时候在我读的那所高中,每个教室后面都放一排桌子供学生放被褥、生活用品等,几张桌子或者一排排凳子一并就是一个床铺,有时候为了抢桌椅同学间也会吵闹、闹别扭。冬天里,白天教室一股饭味、晚上一股脚臭味,总之教室整天基本都是各种大杂烩味道,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铺好铺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盖上聊天戏耍,一位来自北部山区的同学脱下打了若干层补丁的军绿袜子竟然能自己站在桌子上不倒,不知道是因为补丁把袜子的腰杆补硬了还是因为袜子好久没洗、出的脚汗凝固给袜子定了型,反正袜子就是不倒,大家看后嬉笑不止。那几年,周内我们住校生春夏秋冬几乎没人洗脚、晚上更没有人洗嗽了,多少次我早上起来 收拾好铺盖卷坐到座位上进行晨读的时候都发现我的课桌上有清晰地光脚印,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脚臭味,咋办?一笑而过,赶紧背单词吧,考大学事大,哪有时间纠结这些琐事,那时还没进城打工这一说,考不上大学就回家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不说,还要努力种庄稼换钱娶媳妇生个男娃出来,这才能算是对得起父母,这就是当时农村青年人的命运。

一晃高中三年就过去了,幸运的是从我们上两届开始国家取消了高考预选,对大多数同学来说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利好和如雷贯耳的福音。常说高考考场如战场,多少优秀的学子因为种种原因就是没能通过预选这一关,终生都没能跨入正式的高考考场,饱含遗憾的在旧农村里种地、生儿育女式地窝了一辈子,换句话说,预选这个制度怪胎毁了多少国家的栋梁之才!
坦率地说,我们那个年代的高考确实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顺利通过的是少数,那时的农村高中应届生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一个班甚至整个年级全军覆没是常事,不是我们没拼命学,是因为录取率太低,2017年陕西省高考人数近乎32万,大专以上计划录取约28万人,我高考那年陕西省高考人数约25万左右(记不清了),大专以上录取3万多一点点,这就是原因。当时不少父母孤注一掷,家里什么事也不干专门供孩子学习,举全家之力支持孩子补习考大学,当时流行用“几年抗战”这个说话来描述补习生,肩负重托的同学抱着即使把板凳坐穿也要把大学考上的决心,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的同学们陆续通过几年补习,大多数最终都步入了大学的课堂,今天都工作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我们这一代人考大学的经历就是标准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真实写照。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爱拼才会赢,上世纪的高考让多少农村家庭的生活应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著名论断。
抱着抗拒的心理终于熬过了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高中生活,所以高考一放假便逃也似地离开了学校回家,坐等7月7号的到来,当然我也随主流,应届落榜,成绩公布后也没去学校看成绩,一门心思地做好了去立城补习的准备,就是觉得去立诚学习心情好、气顺、离家近。长话短说,到了立城才静下心来,才彻底弄通弄懂了公式定理的含义,记忆力也一下子好了起来,学起习来感觉脑子好使多了,成绩也提高很快,当然最后也如愿以偿,超出重点线40多分,记得那年是8月22日收到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尽管不是心仪的学校,但总算圆了大学梦,没辜负父母省吃俭用一门心思供我跳农门的决心和家庭的重托 ,至今都记得母亲在我应届落榜后说的话“不管咋说咱要把大学考上”,如今工作了好多年了,条件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子欲孝而亲不在,人间的大憾。
絮絮叨叨一大堆,尽管都是些小事,但在我的生命里会永远印记下去,把我们这一辈人攻占高考重地的经历说叨下去,勉励自己、激励后人,这或许算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后辈们最有味的心灵鸡汤。
南湖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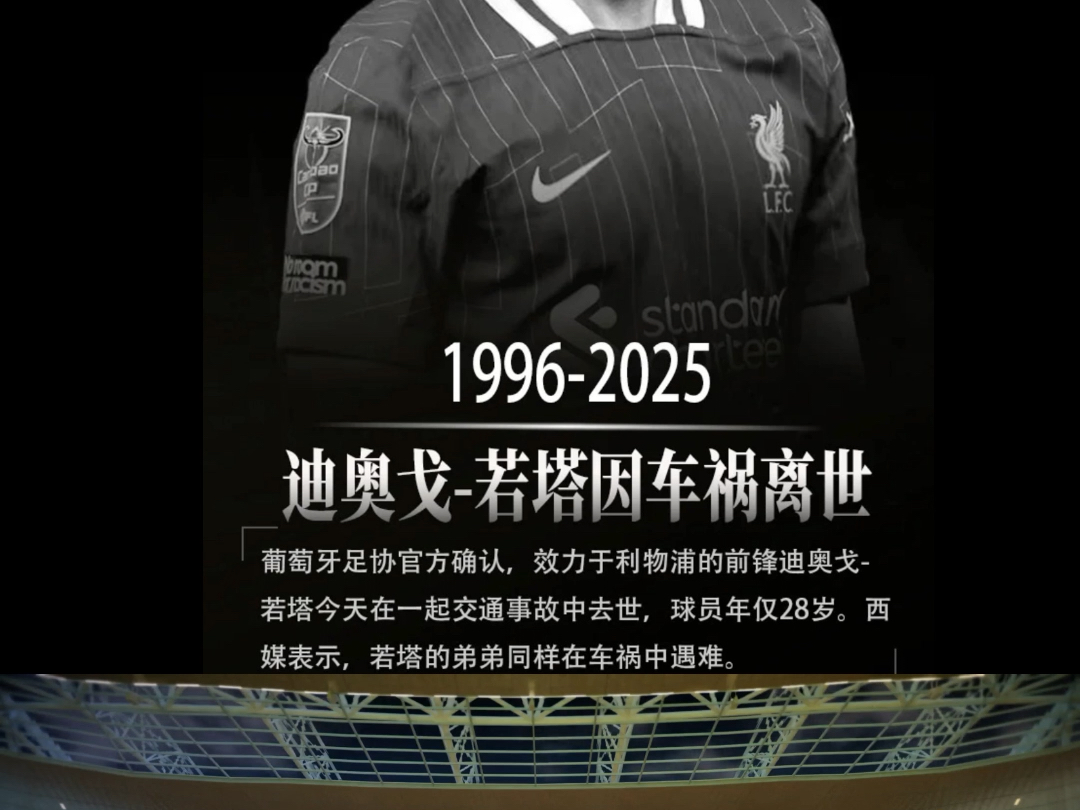

评论留言
暂时没有留言!